文•郭漢丞
前往北京採訪瑞鳴唱片,製作人葉雲川安排了一行人參訪錄音過程,我們在一旁觀察見學,而錄音場地的掌舵人,就是北京中央電視台的錄音師李小沛。在北京的採訪聊了很多,在其中最重要的觀念,李小沛點出:「錄音不僅是技術,更是藝術,當中有音樂美學的審美觀存在著。」成一家之言的關鍵也就在此。
從事錄音工作將近30年
談起何時進入錄音工作,李小沛說他1980年代初期就投入錄音工作,當時他才不過19歲,工作崗位就在北京中央電視台,一路就這麼走過來。不過當時李小沛的主要工作並不是做音樂錄音,而是做很多與影片相關的錄音工作,大約在1982年左右,中央電視台開始建構錄音室,音樂相關的錄音工作才逐漸增加。
從事錄音工作多年,我問李小沛,現在的錄音和過去有何不同?他說早年的錄音工作形式和現在其實差異不大,但內容比較不一樣。早年樂器種類比較沒那麼多,對多軌錄音的需求也比較少;而現在的樂器種類很多,對多軌錄音的需求也比較多。所以早年錄音大約都是找個樂隊來,在錄音室裡面一次錄完,過去的錄音室很多都隔成許多小房間,直接演奏收音即可。但現在錄音的創作內容越來越多樣化,製作所需要的工作就越來越多。李小沛說,以前交響樂團的演奏很重要,一次演出就要達到完美,錄音好不好,就看樂團演奏時究竟有多完美。但現在製作的技術越來越多,後面可以修飾的東西很多,呈現出來的面貌也有些不同。
單點錄音v.s多點錄音
在中央電視台大錄音室裡觀察瑞鳴錄製唱片的過程,只見李小沛在480平方米的大錄音棚內進進出出,調整著麥克風的位置,而且一次只錄製一項樂器,我們可以瞭解這是分段錄音,最後再由錄音室混音製作。這裡點出了錄音手段的差異,對發燒友而言,譬如MA、Chesky、Proprius等等,都推崇單點錄音,拿兩支麥克風找到最佳收音點,標榜接近雙耳聆聽音樂的真實與自然。不過李小沛在中央電視台的錄音方法,很明顯是多麥克風錄音,而且使用很大的錄音棚分段錄製單一樂器,最後再由錄音師透過製作的手段,呈現最終的音樂風貌。
 |
這雙麥克風對多麥克風的問題,其實牽涉到觀念的不同。李小沛表示,過去的錄音業界非常推崇雙麥克風的錄音,這種錄音方法非常自然,他以前也愛用。李小沛說:「用單點錄音,我會花很多的時間,調整樂團或演奏者在錄音空間當中的相對位置,讓演奏者在空間中可以發出很好的聲響,樂器中間還會擺設各種隔音板,營造出定位感,然後回到錄音台聆聽,再要求演奏者調整自己的位置,請他們向左移或向右移。這樣的錄音聽起來能讓演奏者和樂器的定位很準確、很自然,但是實際看看錄音室裡面是怎麼樣的相對位置,那倒是和最後的結果很不一樣。」李小沛認為,單點錄音的方式並不表現錄音者的審美意識,而是盡可能將音樂演奏的自然狀況呈現出來。
用大空間營造錄音的空間感
可是李小沛也認為,錄音其實本身就是一種創作,透過多點錄音,最後製作時可以用很多方法來「擺設」,譬如決定哪一項樂器做主體,哪一項樂器做背景,前前後後,位置都可以重新整理。李小沛的方法是拿一個單獨的樂器來標示空間,譬如找小提琴來當標示,把空間感放進去,那音樂的層次和空間的相關性就出來了。或者特別找一樣樂器來標示細節,把這項樂器最細微的聲響標示出來,好像照片連皮膚上的汗毛都看得見,實際聽起來時大家就會說:「哇!這聽起來真好!」
 |
|
李小沛利用480平方米的大錄音棚營造出錄音的空間感。 |
為了讓錄音後面的製作可以有更多的彈性,李小沛選擇用很大的錄音室去錄製單一的樂器,這點就很不一樣了。一般錄製單一樂器多半在小空間裡錄製,近距離拾取演奏的細節,不過李小沛的方法則是用大空間營造出錄音的空間感。李小沛點出了兩個觀念上的差異,就是「大空間長混響」與「小空間近音源」兩者的不同。
李小沛說,小空間近聲源對單一樂器錄製來說,很多人會採用,有它的優點,但也並不是沒有缺點。小空間近聲源錄單一樂器,大部分只收到樂器本身的訊息,也就是直接音,但卻無法收錄空間的殘響。但大空間錄製單件樂器,可以增加空間感,但並不是沒有問題,長混響一定會影響到樂器本身的收音。所以只要能去除這項困擾,就能兼顧樂器直接音和空間殘響。
錄音是創作,當中包含審美意識
在採訪之前,我們已經聽過古箏的錄製過程,李小沛舉剛才的古箏為例:「剛剛聽古箏的錄音,那音像形體顯得特別的大,特別的活靈活現,還有適當的空間感,但是我最後製作時不會把那麼大的古箏形體全部保留下來,而會將樂器形體收斂起來,把線條做出來,這樣保留了後期製作很大的餘裕度。」
接著,李小沛把「錄音是創作,當中包含審美意識」的想法帶了出來。李小沛說,錄音製作的手段,要從審美需求出發,當我們有審美上的需求時,就去找出手段,但有時候手段不一定能夠滿足審美需求。「譬如我們要把皮膚上細微的汗毛都表現出來,但錄音本身就沒有這些細節存在,那麼再怎麼靠錄音製作的手段,也無法把細節重現。所以我們在錄音的時候,就盡可能把完整的音樂細節錄出來,當我們需要非常真實的細節時,就可以派上用場,但當我們不需要這麼多細節,要當背景陪襯時,也有機會可以把細節去除,但重點是,如果錄音本來就沒有所需的細節,是怎麼樣也無法靠錄音器材變出來。」
好,講到這裡,我們大概可以瞭解為何瑞鳴唱片的錄音,不僅有很優秀的樂器形體,同時有寬闊的空間感,原來每一項樂器錄製時,本身都已經帶著大錄音棚裡面的空間殘響,而李小沛在製作過程中,只是刪減過多的殘響,拉出音樂的線條感,彷彿畫家在修飾畫面物件比例一般,既見樹又見林。
數位錄音v.s類比錄音
參觀中央電視台的幾個錄音室,不難發現這裡的專業器材幾乎都是目前最好的,自然在這裡也是走全數位錄音。雖然我們有看到很多經典的盤帶錄音機,但那些器材基本上都已經退休。我問李小沛,他認為數位錄音比較好,還是類比錄音比較接近原汁原味?李小沛的回答很妙:「社會是要發展的,科技是要發展的,不能抱著古老的技術,就不想往前走。數位錄音的技術確實解決了許多的問題,我們只是要盡可能發揮數位錄音的優點,同時想辦法保留類比錄音的好處。」
李小沛談到類比錄音的難題,他說類比錄音過程複雜、中間損失多、噪訊比不佳、
機械操作困難、成本過高,這些都是早年類比時代存在的問題,必需解決,而解決的辦法就是數位錄音。李小沛認為現在已經不討論數位好還是類比好,只問數位錄音最後要怎麼保留類比錄音最好的部分。譬如類比錄音本身就是絕對的正弦波,而數位的方波就算你再怎麼精密的計算,那正弦波的弧線還是有細微的鋸齒狀。可是現在已經不比較類比好還是數位好,而是要問哪一種數位錄音格式比較接近類比,究竟該繼續使用CD的PCM還是SACD的DSD,那就是數位手段中的選擇了。
器材只是錄音時的手段
看著中央電視台的錄音室,配備了最新的Prism Sound DSD錄音設備,而且瑞鳴的唱片包括了標準CD、XRCD與SACD,本以為這裡會使用DSD錄音,但李小沛透露,他們還是使用PCM的格式。李小沛說,在錄音工作中不要和自己過不去,用PCM格式錄音全世界通行,需要DSD另外再來轉,這很實際的考量。
一般走訪錄音室,很多錄音師都會介紹自家的器材,但我發現李小沛對於器材並沒有那麼熱衷,或者說,器材的使用只是李小沛在錄音時的手段,看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,他就會使用怎樣的手段。這和李小沛認為「錄音是創作!錄音是美學!」的觀念有關。我問李小沛,究竟什麼時候興起「錄音是藝術」的想法,他說已經記不起清楚的時間點了,不過大約是在電子樂器越來越多加入錄音工作時,才發現原來音樂可以做成這個模樣。
追求錄音創作的整體面貌
李小沛說,其實他也是跟著時間慢慢轉變的,也受到市場很多教育,尤其在「發燒」這件事情,受教最多。他想起以前作錄音,比較像是生產工作,早期都是跟著製作人或唱片公司的想法,把音色調亮一些、調暗一些,哪裡增加一點、哪裡減少一點,但後來自己的程度越來越進步,慢慢地製作人就不指點哪裡要調整,而是溝通想法。以前總是想盡量滿足發燒友的需求,把定位、質感等等做好,但現在已經不一樣,李小沛在錄音時會從音樂出發,試著把某些關鍵元素突顯出來,把場面做出來,等風貌浮現了,接著就是讓發燒友去品味評鑑,聽聽看這樣錄音的整體好不好。如此一來,錄音師的創作就有整體的面貌,而不是追求很多單一的項目。
李小沛說他現在做有自我審美觀的錄音,是希望讓發燒友聽整體,而不是專門看手腳,現在讓大家看全身。一開始做錄音,只追求音質、音色,後來追求的東西越來越多了,到最後才發現自己所要追求的是更高的目標,而不是跟著發燒友的想法單純去滿足而已,這時候錄音師的程度才會向上提升,比發燒友層次更高,也才能進入創作的狀態,想著去表現錄音師的審美觀。這樣做錄音,完全進入另外一種狀態,要有自己的觀點、自己的想法,告訴聽眾你的審美觀是什麼。李小沛認為他從製作發燒唱片的過程中學到很多,但實際上也是發燒唱片的製作經驗,提升了他的錄音水準,想出「錄音是創作,錄音是藝術」的哲理。
現在李小沛做錄音,拿到素材會先問這是錄什麼樣的音樂,然後思考一下,想想該怎麼表現。李小沛說這很多要靠經驗,例如和瑞鳴的合作,唱片內容是傳統戲曲,他要先想想這到底是什麼,怎麼表現,每一項樂器加進來之後,都要問這項樂器究竟扮演怎麼樣的角色。究竟這項樂器是主奏、背景、旁枝、骨幹,搞清楚了,再把收錄進來的音樂先行處理,做出一個雛形,然後和製作人討論,究竟是不是符合樂曲的主旨。
這種創作是固定模式還是變化多端?李小沛說他在每一張唱片裡面,即使是相同類型的音樂,使用的方法也都不盡相同,但李小沛並沒有和唱片公司講,也不多做解釋,只把結果呈現出來。譬如絲竹類的樂曲,李小沛說他幫許多唱片公司製作過這類型唱片,但每一張錄音個性都不同,有的要表現細節,有的追求質感,有的表達意境,但他都沒有多做解釋,實際去聽就能聽出差異。
兩聲道v.s多聲道
在李小沛的錄音作品中,幾乎都是兩聲道的錄音,我問李小沛,錄音的演變有沒有可能多聲道迎頭趕上?答案也很有趣,李小沛說:「當人們聽過多聲道的錄音,也越來越熟悉之後,答案就越來越清楚了,這不是天天可以吃的飯。或許偶而聽一下很刺激,但天天聽或許不太適合。」
此話怎說?李小沛說兩聲道的錄音目標很清楚,就是盡可能透過錄音的手段,重現音樂現場的氣氛與場景,但是在多聲道的錄音中,目標就很不確定了,究竟要把音樂營造成包圍聆聽者,還是讓聆聽者感覺音樂舞台在前方,樂器相對的位置究竟該怎麼擺,對錄音或混音工作而言都可以做到,但這樣做究竟好不好,或是能不能符合聆聽者的習慣,沒有一個標準。所以最後演變成錄音師自己玩,用自己的想像和情境設定,帶來不一樣的多聲道聽感,可是交給聆聽者評判時,如果不能讓大家聽習慣,很難讓市場接受。講到這裡,答案出來了,在兩聲道的錄音中,真實自然已經是準則,加上一些美感還可以接受,但多聲道目前還沒準則。
我很好奇,李小沛似乎很少參與大型交響樂團的現場錄音作品,不過李小沛說,他其實錄過很多年現場的交響樂,但他已經放棄不想錄了。他認為錄交響樂團沒有創作,而且過程中費盡了所有錄音的手段,還是不如現場,交響樂有太多細節,太難配合了。譬如樂隊不是很好、空間不是很好、樂器不是很好,錄音師所有的勁都使在這上面,想把樂團的音色平衡起來,但原來的聲音就不夠好、不夠平衡,錄音師要想辦法把它弄得很好,這哪裡有辦法。李小沛表示,國外有很多好的交響樂錄音,那些有很棒的場地搭配著第一流的樂團,但這樣一來錄音師的本領也就派不上什麼用場,選好的麥克風,照教科書的方法擺設起來,錄音自然水準就有。「所以問我想不想再去錄製交響樂,坦白說,還真不想去做。」李小沛如此說道。
不僅是技術,也是藝術
在北京中央電視台與李小沛對談,闡述了錄音不僅是技術,也是藝術的觀念。在北京中央電視台的大錄音棚中,耗時費力地收錄每一項樂器的演奏細節與空間殘響,透過李小沛與葉雲川共同的審美觀,匯集出瑞鳴唱片的生命力。或許,你現在就可以找一張瑞鳴的唱片,不管是「粉墨是夢」或「伶歌」,試著在自己的音響系統上,體會李小沛的錄音藝術。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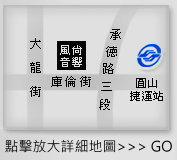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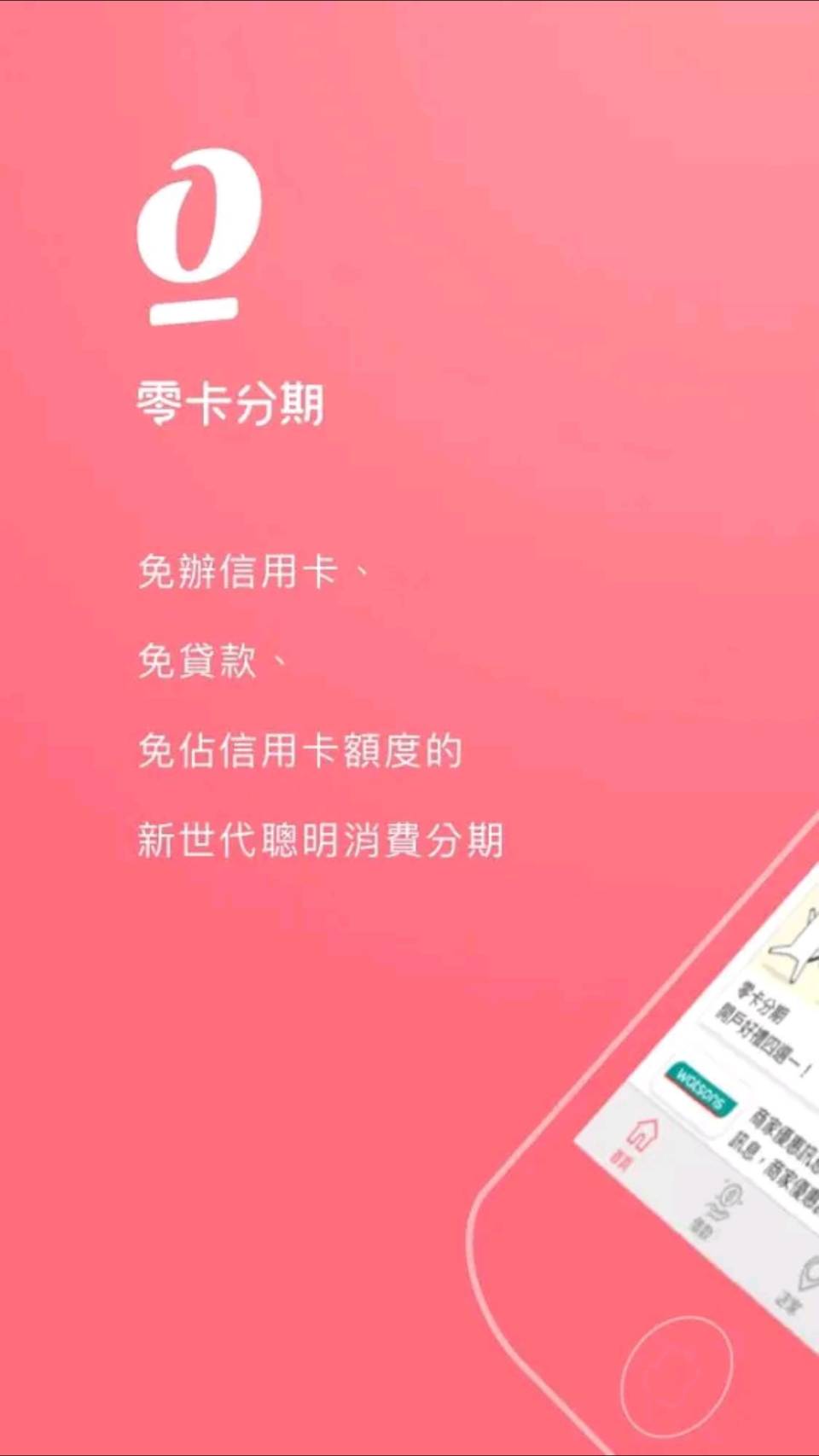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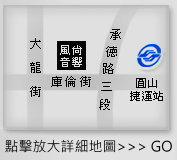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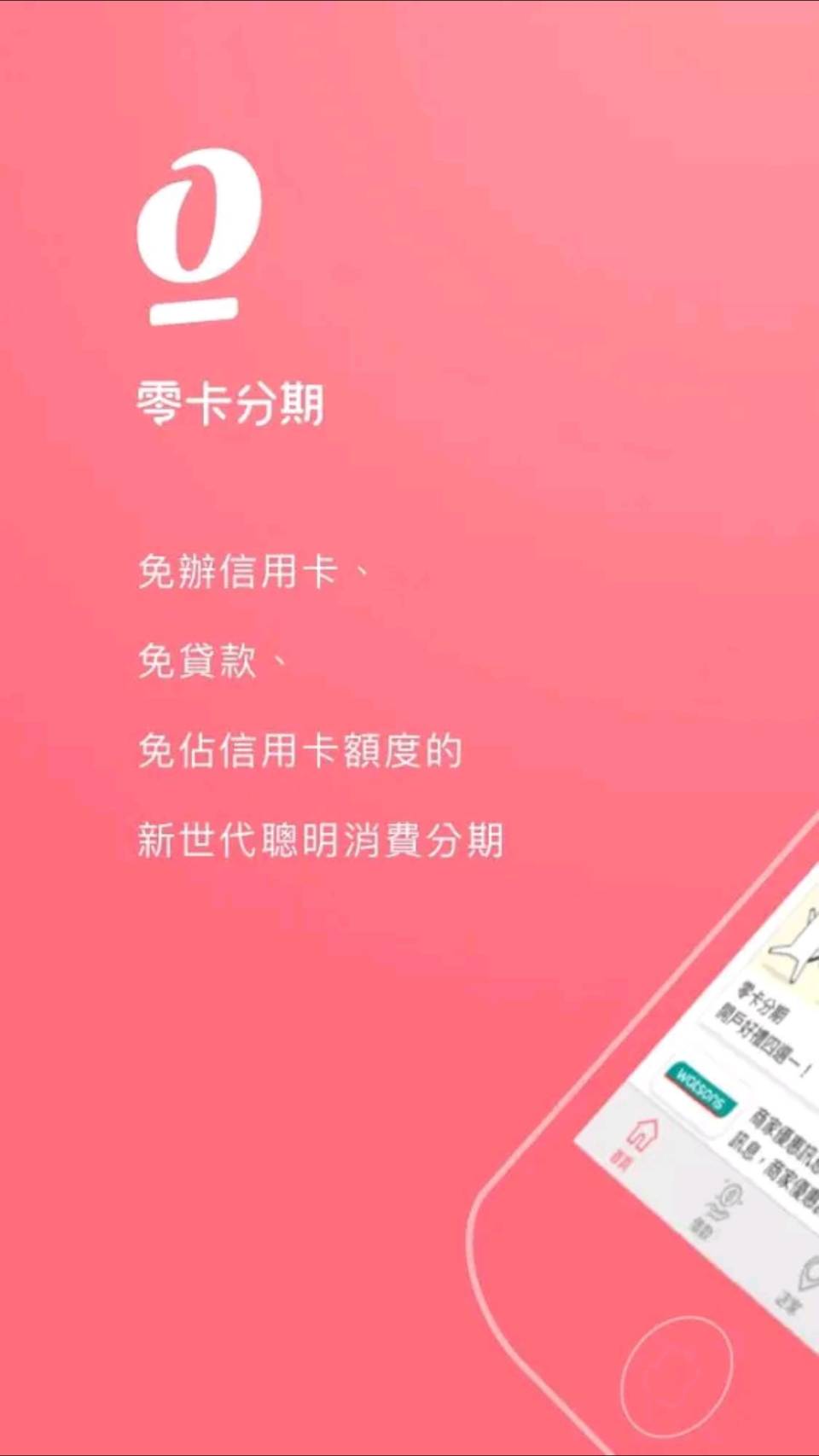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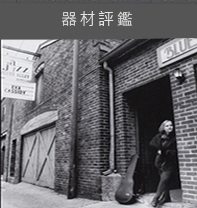
 音響評鑑
音響評鑑 綜合擴大機評鑑
綜合擴大機評鑑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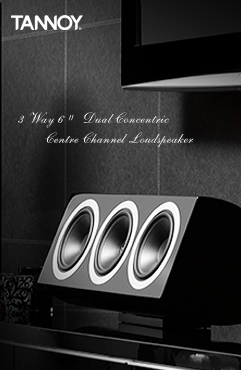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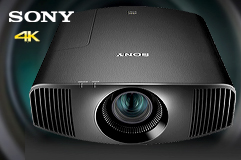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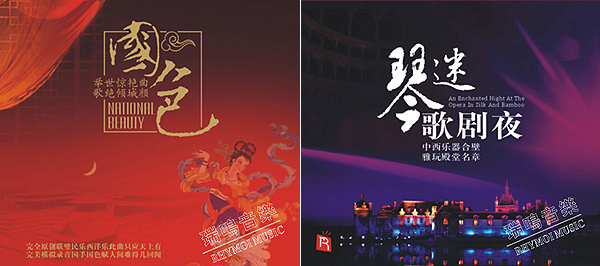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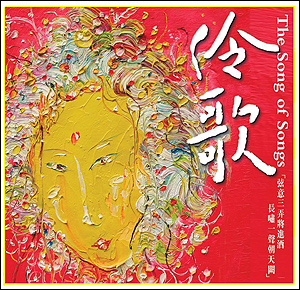


.png) 回上一頁
回上一頁.png) 回評鑑首頁
回評鑑首頁.png) 加入最愛文章
加入最愛文章